【河东文化】玉泉寺的历史回声
发布时间 2025-07-17 18:05:42
详细描述
分类主题: 凤城往事
一
我知道,这注定是一场毫无结果的寻访。我们要寻访的主人公,已经牺牲87年了。但我们还是来了,顺着一条新修的山路,从风柏峪迤逦进入中条山深处。山的颜色与溪水的颜色交相辉映,那鼓满山歌的风吹过这片山口,山口腾起白色与灰色的云气。
一阵急雨,把满山洗得更绿。到处是核桃、香椿、板栗、西红柿和玉米,金银花在风中发出金属的响声。山上,陡峭的、倔强的红色断崖忽隐忽现。水从高处倾泻而下,流成了欢快的瀑布。
山路顶端就是我们要寻找的玉泉寺。说起玉泉寺,我就想起李家骥,当年玉泉寺一战,让李家骥名垂千古;想起李家骥,也总想寻找那抗日的硝烟,寻找国民革命军九十六军四十七旅七四一团那些为抗日牺牲的英烈们。
1938年日军占领虞乡,为打通中条山南北通道,驱使山北虞乡、山南芮城两县数千民夫,从风柏峪村开始修建盘山公路至山南芮城县。
如果没有战争,那就是一个宁静的冬天。但那虚幻的平静很快就被彻底打破了。正值腊月,中条山下风柏峪村13岁的王锁和几个小伙伴相约上山,准备套些野兔过年。一大早推开柴门,却被一伙日本兵抓住,押到山上修路,王锁走在队伍里,被推搡着,谁知就顺山崖滚下去了。
家里人听说孩子被日本鬼子祸害死了,哭成一团。第二天晚上,王锁却从山崖下一点一点爬回家,仇恨地说,老天爷呀,咋不劈死这天杀的鬼子。几天后,中国军队从陕西过来打跑了鬼子兵,在风柏峪村外和山上玉泉寺驻扎。王锁他们几个认识了大个子李团长,目睹了李团长带领士兵给村民担水、修房屋,在打麦场与士兵操练拼杀,饭前和睡觉前一起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曲,激励中国军人的斗志,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当地村民和中国军人同生死、共患难,谱写了一段鱼水情深的军民情。
二
王锁记得玉泉寺的枪炮声是从1939年1月23日天麻麻亮时响起,雪花不住地飘,黄乎乎的鬼子兵从风柏峪山路往上攻。这是驻守运城的日军川岸师团七十七联队和八十联队,分六路向驻守在中条山的中国守军发起大扫荡。扫荡的重点就是中条山西段防线,即玉泉寺、白庙岭、苍龙峪、二里岭一线。而四十七旅七四一团的玉泉寺阵地是敌人进攻的必经之路。
玉泉寺位于中条山五老峰之东,与山北虞乡、山南芮城构成一条斜线上的三个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军分别从山南、山北各个峪口进攻。战前,李家骥得到中国共产党虞乡县委传递的情报,经过认真分析,明白敌人就是要撕开中国守军的防线,为来年开春发动全线进攻扫清障碍。李团长采用阵地战与运动战结合的战术,行动飘忽、难以捕捉,率部如定海神针,死死顶住日军的狂攻。
李家骥是河北省静海县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加入西北军杨虎城部。1938年奉命从陕西合阳镇东渡,率部北袭万泉、夜取河津、强占荣河、夺回安邑,嵋阳之战中又率部重创日军,屡战屡胜,令敌胆寒。
他记得出征河东临行前跪在老娘面前说:“娘,儿子给您老磕头,我要打仗去了!”“儿啊,咱村里人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你可不敢给咱趴下,叫咱家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别操心娘,娘好着咧,等你打完鬼子,娘天天给你做油泼辣子擀面。”多么简单而朴实的道理,没有任何多余的语言去形容那种震撼。那个年代,有多少个娘送走了老大再送老二。娘啊,噙着泪,把自己身上的一块肉送走了,还不够,一声噩耗之后,又把另一块心头肉送走。娘是伟大的,那些送子杀敌寇的娘更是伟大的!
抗战时期,无数将士像李家骥一样,告别家人,毅然奔赴抗日前线。他们用自己对民族的忠诚,用热血和生命,展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勇御外侮的铮铮铁骨。
三
我们上山后,沿一条蜿蜒的小路看到了玉泉寺遗址。该寺始建于唐代,曾是佛教活动中心。据说眼前这片上千亩高山梯田与窑洞村落、寺庙遗址,就是昔年李家骥抗击日军的战场。枪炮声声,日寇五六千人向玉泉寺阵地猛烈进攻,敌机轮番轰炸扫射。因为没有防空设备,战士们伤亡惨重……李家骥和战友们没有丝毫畏惧,拼命守护着阵地。他沉着指挥,带领将士浴血奋战,所守阵地五日五夜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不计其数。最后,敌寇竟卑劣地释放毒气,七四一团被包围,弹尽粮绝,官兵伤亡严重,援军也被阻于芮城东二十里,无法救援。随着呐喊声,一群陕西“冷娃”冲下山坡。一场白刃肉搏战开始了,开始时,战士们和鬼子拼刺刀,刺刀挑弯了,就抱住鬼子挽蛋子。一场拼杀持续了十几分钟,李团长振臂挥枪,毙敌十余人后壮烈牺牲,将三十九岁的生命,献给了中条山及抗日烽火。
李家骥倒在雪地上,剩下的百余名士兵也倒在了雪地上……鲜血将雪地融化,浸染成一条条溪流,“血溪”中有中国士兵的血,也有日本士兵的血。中条山见证了悲壮,也见证了罪恶。这是一个雪后初霁的清晨,太阳照亮了这片战后宁静的山河,随即又躲进云层里暗自饮泣。
战死的兄弟有的和鬼子抱在一起怎么也分不开,有的身中数枪仍靠在工事边屹立不倒,有的怒目圆睁端着枪……他们一个个保持着催人泪下的姿势。几十年后,幸存下来的那个士兵总会做一个相同的梦,在梦里,兄弟们穿着制服吼着,从他身边列队走过去。每次梦到这个地方,他就会醒来,坐起来,倾听身边妻子那熟睡的温柔的鼾声,心底总有一滴泪。
日军撤退后,中共虞乡县委、县牺盟会根据党的指示,带领抗日人民自卫队,号召、发动附近的风柏峪、王官峪、扶窑村的村民,冒着严寒,踏着积雪连夜赶到山上。玉泉寺只剩下一垛墙壁和残砖碎瓦。四周静悄悄的,山上的残雪泛着模糊而清冽的寒光,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和血腥味。
村民们跪倒在结着冰凌的“血溪”前,跪在浑身是血、残肢断臂的七四一团士兵遗体前放声大哭。他们在山坡上寻找同袍弟兄的尸身,不忍让他们陈尸山野,凡找到的,或背或抬,都款款运下山。王锁和伙伴也在其中,他一直活到2021年,生前总给子孙们讲日本鬼子祸祸老百姓罄竹难书的罪行和李家骥率军在玉泉寺浴血奋战、壮烈殉国的事迹,每每潸然泪下,直言那段历史沉重得不忍回顾。
王锁的娘听从虞乡县牺盟会安排,抛下吃奶的小孩子,把一名奄奄一息的战士藏进山洞,每日为他清洗伤口,送水送饭。全家吃糠咽菜,王锁和小伙伴整日套野兔、抓野鸡,由娘做菜熬汤,为伤兵补充营养,最终使他伤愈归队。这是娘的本能,也是她的真情。娘啊,就如那些山间的杜鹃花,散发着自带的清香。
搜索人员把李团长的遗体抬上担架,有个小媳妇掏出毛巾,蘸着雪水,为李团长擦拭脸上的淤血。她的手很轻很轻,似乎怕惊醒睡梦中的英雄,泪水却洒落在英雄的身上。痛,是那样的痛,如同利箭穿心而过,几个负伤的士兵跪在李家骥遗体旁嚎啕大哭,村民们也齐刷刷地跪了,哭声一片。一团团雾气不时飘浮过来,就像为英雄送来一幅挽幛。
为了不让牺牲的英雄露尸荒野,中共虞乡县委和县牺盟会召集当地村民将遗体安放在虞乡石佛寺旁几座废弃的窑洞里,就地掩埋。德高望重的族长,捐百丈绫,献三牲礼,焚香灵堂,头裹孝布,引乡亲,领族人,三叩九拜,身暖寒窑,为英灵祈祷送行。纸钱飘飘,香烛摇曳,村民们流着泪端着饺子到灵前,祭奠长眠在中条山牺牲的英雄。
这里牺牲的每一位中国军人,都可以用英雄来称谓,他们铸成一座英勇的丰碑,使日本鬼子难以逾越中条山一步。这些牺牲的士兵,昨天还和家人牵牛耕地或挥镰割麦,听到召唤,拴上牛收起镰就走出柴门,走进军营换上军装,端起武器杀敌寇,成为日本鬼子绝难前进一步的壁垒。
虞乡县牺盟会组织16个村民用担架抬着李家骥的遗体翻山越岭,一直送到平陆县葛赵镇部队。当年2月3日,国民革命军第九十六军在葛赵镇的黄河岸边召开追悼大会,军长李兴中将军说:“玉泉寺战役,李团长亲率官兵浴血奋战,壮烈殉国,给敌以重创,迫使敌人后撤。掩护了我第四集团军及其他友军,维护了陇海铁路交通安全,巩固了黄河防线,缓解了敌人对潼关和陕东的威胁。李团长的战功是永不磨灭的,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典范!”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将军亲手书写挽联:“雪压冬云青松昂首断臂壮士忠魂不灭;雾锁苍山战马扬鬃打虎英雄豪气永存。”在平陆指挥作战的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将军赋诗:“妖气弥漫寇方张,百战何辞作国殇。士卒冲锋杀敌处,娘子关外月如霜。”
九十六军官兵含泪振臂高呼抗日口号,追悼会成为誓师会。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李家骥为革命烈士。敌寇入侵,金瓯残破,为了爹娘,为了家国,一个个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挺起了伟岸的胸膛!不能忘啊,也忘不了。这就是历史,让我们和后代记住吧。
四
听当地人说,每年清明节,王锁老人都会陪伴年轻人来这里祭奠英烈。80多年过去了,淳朴善良的乡亲们用这种方式来铭记过去、教育后人,可见李家骥一直是珍藏在他们心中的抗日英雄。
虞乡高山梯田如锦缎,每个季节都有着不同的美丽和品质,春夏的绿,秋天的黄,冬天的白……动中有静,静中含芳。当地政府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核桃、香椿、西红柿、中药材等产业,“虞乡”农产品已成为永济原生态农业的亮丽名片,远销北京、上海、太原、西安等大中城市,深受消费者青睐。眼前上山的道路已提升改造,并与中条山沿山路(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支线)相连接,乡村振兴、红色旅游、原生态农业发展和农民致富……古老的山村正在发生璀璨的蝶变。
太阳冉冉升起,喷射出绚烂的朝霞,把连绵起伏的群山映红,也把山下的涑水河映成了一道长长的绸带。我不觉向脚下的土地投以深情的一瞥:中条山抗战的枪声穿越时空,被永远刻入历史的年轮,它见证的不仅是奋起的抵抗,更是一个民族在危难中的觉醒与凝聚,这份凝聚力,已淬炼进民族基因的最深处,穿透时光,直至今天,及至未来!
张继龙 秦冰荣/文
我知道,这注定是一场毫无结果的寻访。我们要寻访的主人公,已经牺牲87年了。但我们还是来了,顺着一条新修的山路,从风柏峪迤逦进入中条山深处。山的颜色与溪水的颜色交相辉映,那鼓满山歌的风吹过这片山口,山口腾起白色与灰色的云气。
一阵急雨,把满山洗得更绿。到处是核桃、香椿、板栗、西红柿和玉米,金银花在风中发出金属的响声。山上,陡峭的、倔强的红色断崖忽隐忽现。水从高处倾泻而下,流成了欢快的瀑布。
山路顶端就是我们要寻找的玉泉寺。说起玉泉寺,我就想起李家骥,当年玉泉寺一战,让李家骥名垂千古;想起李家骥,也总想寻找那抗日的硝烟,寻找国民革命军九十六军四十七旅七四一团那些为抗日牺牲的英烈们。
1938年日军占领虞乡,为打通中条山南北通道,驱使山北虞乡、山南芮城两县数千民夫,从风柏峪村开始修建盘山公路至山南芮城县。
如果没有战争,那就是一个宁静的冬天。但那虚幻的平静很快就被彻底打破了。正值腊月,中条山下风柏峪村13岁的王锁和几个小伙伴相约上山,准备套些野兔过年。一大早推开柴门,却被一伙日本兵抓住,押到山上修路,王锁走在队伍里,被推搡着,谁知就顺山崖滚下去了。
家里人听说孩子被日本鬼子祸害死了,哭成一团。第二天晚上,王锁却从山崖下一点一点爬回家,仇恨地说,老天爷呀,咋不劈死这天杀的鬼子。几天后,中国军队从陕西过来打跑了鬼子兵,在风柏峪村外和山上玉泉寺驻扎。王锁他们几个认识了大个子李团长,目睹了李团长带领士兵给村民担水、修房屋,在打麦场与士兵操练拼杀,饭前和睡觉前一起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曲,激励中国军人的斗志,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当地村民和中国军人同生死、共患难,谱写了一段鱼水情深的军民情。
二
王锁记得玉泉寺的枪炮声是从1939年1月23日天麻麻亮时响起,雪花不住地飘,黄乎乎的鬼子兵从风柏峪山路往上攻。这是驻守运城的日军川岸师团七十七联队和八十联队,分六路向驻守在中条山的中国守军发起大扫荡。扫荡的重点就是中条山西段防线,即玉泉寺、白庙岭、苍龙峪、二里岭一线。而四十七旅七四一团的玉泉寺阵地是敌人进攻的必经之路。
玉泉寺位于中条山五老峰之东,与山北虞乡、山南芮城构成一条斜线上的三个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军分别从山南、山北各个峪口进攻。战前,李家骥得到中国共产党虞乡县委传递的情报,经过认真分析,明白敌人就是要撕开中国守军的防线,为来年开春发动全线进攻扫清障碍。李团长采用阵地战与运动战结合的战术,行动飘忽、难以捕捉,率部如定海神针,死死顶住日军的狂攻。
李家骥是河北省静海县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加入西北军杨虎城部。1938年奉命从陕西合阳镇东渡,率部北袭万泉、夜取河津、强占荣河、夺回安邑,嵋阳之战中又率部重创日军,屡战屡胜,令敌胆寒。
他记得出征河东临行前跪在老娘面前说:“娘,儿子给您老磕头,我要打仗去了!”“儿啊,咱村里人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你可不敢给咱趴下,叫咱家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别操心娘,娘好着咧,等你打完鬼子,娘天天给你做油泼辣子擀面。”多么简单而朴实的道理,没有任何多余的语言去形容那种震撼。那个年代,有多少个娘送走了老大再送老二。娘啊,噙着泪,把自己身上的一块肉送走了,还不够,一声噩耗之后,又把另一块心头肉送走。娘是伟大的,那些送子杀敌寇的娘更是伟大的!
抗战时期,无数将士像李家骥一样,告别家人,毅然奔赴抗日前线。他们用自己对民族的忠诚,用热血和生命,展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勇御外侮的铮铮铁骨。
三
我们上山后,沿一条蜿蜒的小路看到了玉泉寺遗址。该寺始建于唐代,曾是佛教活动中心。据说眼前这片上千亩高山梯田与窑洞村落、寺庙遗址,就是昔年李家骥抗击日军的战场。枪炮声声,日寇五六千人向玉泉寺阵地猛烈进攻,敌机轮番轰炸扫射。因为没有防空设备,战士们伤亡惨重……李家骥和战友们没有丝毫畏惧,拼命守护着阵地。他沉着指挥,带领将士浴血奋战,所守阵地五日五夜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不计其数。最后,敌寇竟卑劣地释放毒气,七四一团被包围,弹尽粮绝,官兵伤亡严重,援军也被阻于芮城东二十里,无法救援。随着呐喊声,一群陕西“冷娃”冲下山坡。一场白刃肉搏战开始了,开始时,战士们和鬼子拼刺刀,刺刀挑弯了,就抱住鬼子挽蛋子。一场拼杀持续了十几分钟,李团长振臂挥枪,毙敌十余人后壮烈牺牲,将三十九岁的生命,献给了中条山及抗日烽火。
李家骥倒在雪地上,剩下的百余名士兵也倒在了雪地上……鲜血将雪地融化,浸染成一条条溪流,“血溪”中有中国士兵的血,也有日本士兵的血。中条山见证了悲壮,也见证了罪恶。这是一个雪后初霁的清晨,太阳照亮了这片战后宁静的山河,随即又躲进云层里暗自饮泣。
战死的兄弟有的和鬼子抱在一起怎么也分不开,有的身中数枪仍靠在工事边屹立不倒,有的怒目圆睁端着枪……他们一个个保持着催人泪下的姿势。几十年后,幸存下来的那个士兵总会做一个相同的梦,在梦里,兄弟们穿着制服吼着,从他身边列队走过去。每次梦到这个地方,他就会醒来,坐起来,倾听身边妻子那熟睡的温柔的鼾声,心底总有一滴泪。
日军撤退后,中共虞乡县委、县牺盟会根据党的指示,带领抗日人民自卫队,号召、发动附近的风柏峪、王官峪、扶窑村的村民,冒着严寒,踏着积雪连夜赶到山上。玉泉寺只剩下一垛墙壁和残砖碎瓦。四周静悄悄的,山上的残雪泛着模糊而清冽的寒光,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和血腥味。
村民们跪倒在结着冰凌的“血溪”前,跪在浑身是血、残肢断臂的七四一团士兵遗体前放声大哭。他们在山坡上寻找同袍弟兄的尸身,不忍让他们陈尸山野,凡找到的,或背或抬,都款款运下山。王锁和伙伴也在其中,他一直活到2021年,生前总给子孙们讲日本鬼子祸祸老百姓罄竹难书的罪行和李家骥率军在玉泉寺浴血奋战、壮烈殉国的事迹,每每潸然泪下,直言那段历史沉重得不忍回顾。
王锁的娘听从虞乡县牺盟会安排,抛下吃奶的小孩子,把一名奄奄一息的战士藏进山洞,每日为他清洗伤口,送水送饭。全家吃糠咽菜,王锁和小伙伴整日套野兔、抓野鸡,由娘做菜熬汤,为伤兵补充营养,最终使他伤愈归队。这是娘的本能,也是她的真情。娘啊,就如那些山间的杜鹃花,散发着自带的清香。
搜索人员把李团长的遗体抬上担架,有个小媳妇掏出毛巾,蘸着雪水,为李团长擦拭脸上的淤血。她的手很轻很轻,似乎怕惊醒睡梦中的英雄,泪水却洒落在英雄的身上。痛,是那样的痛,如同利箭穿心而过,几个负伤的士兵跪在李家骥遗体旁嚎啕大哭,村民们也齐刷刷地跪了,哭声一片。一团团雾气不时飘浮过来,就像为英雄送来一幅挽幛。
为了不让牺牲的英雄露尸荒野,中共虞乡县委和县牺盟会召集当地村民将遗体安放在虞乡石佛寺旁几座废弃的窑洞里,就地掩埋。德高望重的族长,捐百丈绫,献三牲礼,焚香灵堂,头裹孝布,引乡亲,领族人,三叩九拜,身暖寒窑,为英灵祈祷送行。纸钱飘飘,香烛摇曳,村民们流着泪端着饺子到灵前,祭奠长眠在中条山牺牲的英雄。
这里牺牲的每一位中国军人,都可以用英雄来称谓,他们铸成一座英勇的丰碑,使日本鬼子难以逾越中条山一步。这些牺牲的士兵,昨天还和家人牵牛耕地或挥镰割麦,听到召唤,拴上牛收起镰就走出柴门,走进军营换上军装,端起武器杀敌寇,成为日本鬼子绝难前进一步的壁垒。
虞乡县牺盟会组织16个村民用担架抬着李家骥的遗体翻山越岭,一直送到平陆县葛赵镇部队。当年2月3日,国民革命军第九十六军在葛赵镇的黄河岸边召开追悼大会,军长李兴中将军说:“玉泉寺战役,李团长亲率官兵浴血奋战,壮烈殉国,给敌以重创,迫使敌人后撤。掩护了我第四集团军及其他友军,维护了陇海铁路交通安全,巩固了黄河防线,缓解了敌人对潼关和陕东的威胁。李团长的战功是永不磨灭的,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典范!”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将军亲手书写挽联:“雪压冬云青松昂首断臂壮士忠魂不灭;雾锁苍山战马扬鬃打虎英雄豪气永存。”在平陆指挥作战的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将军赋诗:“妖气弥漫寇方张,百战何辞作国殇。士卒冲锋杀敌处,娘子关外月如霜。”
九十六军官兵含泪振臂高呼抗日口号,追悼会成为誓师会。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李家骥为革命烈士。敌寇入侵,金瓯残破,为了爹娘,为了家国,一个个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挺起了伟岸的胸膛!不能忘啊,也忘不了。这就是历史,让我们和后代记住吧。
四
听当地人说,每年清明节,王锁老人都会陪伴年轻人来这里祭奠英烈。80多年过去了,淳朴善良的乡亲们用这种方式来铭记过去、教育后人,可见李家骥一直是珍藏在他们心中的抗日英雄。
虞乡高山梯田如锦缎,每个季节都有着不同的美丽和品质,春夏的绿,秋天的黄,冬天的白……动中有静,静中含芳。当地政府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核桃、香椿、西红柿、中药材等产业,“虞乡”农产品已成为永济原生态农业的亮丽名片,远销北京、上海、太原、西安等大中城市,深受消费者青睐。眼前上山的道路已提升改造,并与中条山沿山路(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支线)相连接,乡村振兴、红色旅游、原生态农业发展和农民致富……古老的山村正在发生璀璨的蝶变。
太阳冉冉升起,喷射出绚烂的朝霞,把连绵起伏的群山映红,也把山下的涑水河映成了一道长长的绸带。我不觉向脚下的土地投以深情的一瞥:中条山抗战的枪声穿越时空,被永远刻入历史的年轮,它见证的不仅是奋起的抵抗,更是一个民族在危难中的觉醒与凝聚,这份凝聚力,已淬炼进民族基因的最深处,穿透时光,直至今天,及至未来!
张继龙 秦冰荣/文
联系人
丁侦球
立即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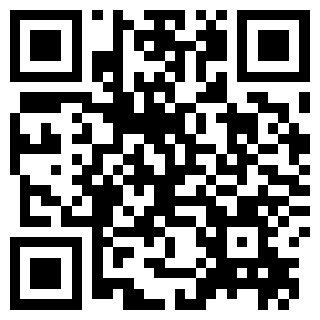
运城社区客户端
查看和发布更多信息。









